 第250章 勿謂言之不預! 首輔
第250章 勿謂言之不預! 首輔
 第250章 勿謂言之不預! 首輔
第250章 勿謂言之不預! 首輔
汪直最重要的軍火和戰船供給,汪直敗象顯露,無奈接受胡宗憲詔安,最後被時任浙江按察使的王本固斬首於杭州。
這裡張經句句不饒人,陸遠也是來了脾氣。
「嘉靖三十一年,汪逆自吳淞口登岸,沿途屠戮我子民,那個時候,張部堂又在做什麼?」
「老夫在積極備戰,準備收復雙嶼。」
「我在問張部堂為什麼會讓汪逆登岸!」陸遠低喝道:「張部堂身為我大明朝的浙直總督,連海防安全都守不住,無法做到禦敵於國門之外,難道不是丟土失職的責任嗎!」
張經氣的面色潮紅:「海線浩蕩數千里,老夫手中僅幾百艘戰船,焉能守得住。」
「哈。」陸遠嘲諷一笑:「守不住您有藉口,是不是給您幾千艘戰船您就能守住了。」
「當然。」
「朝廷若是有幾千艘戰船、幾萬門火炮、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軍隊,還用您來做這個浙直總督嗎!」
陸遠一拍扶手:「本輔家裡隨便去一個家僕當這個浙直總督,也能守住國門了。」
「伱!」張經氣的怒然起身,指著陸遠:「你欺人太甚。」
「本輔說事實,張部堂聽不得,張部堂說藉口,就要求別人都得聽進心裡去。」
陸遠微微仰頭,眼神里滿是不屑和譏諷:「張部堂好霸道啊,這些年本輔做的所有事,都是為了你張部堂能儘快剿滅汪逆,這些您看不到,您看到的只是陸某裁了你的總督衙門,讓你張部堂一夜之間少了十幾萬的兵權,所以你對陸某百般的不爽和憤懟。
當年本輔還在做浙江按察副使的時候,你張部堂幹了什麼事,你越過浙江臬司衙門召見本輔,讓本輔去協調浙江藩司為你籌措糧餉,你安的是什麼心?你現在敢不敢摸著自己的良心說一句,你全無私心?」
「老夫仰不愧天、俯不愧地,有什麼不敢。」張經大聲道:「老夫一心就是為了替皇上和朝廷剿除奸逆。」
「那你知不知道強行征糧會使多少老百姓家破人亡!」
陸遠也站了起來:「你敢說不知道嗎。」
張經被懟的啞口無言。
「你們這些人,呵呵。」陸遠冷笑道:「動不動就是那一句先苦一苦老百姓,當年要不是陸某自掏腰包給你填窟窿、補虧空,你打個屁的仗,他娘的,現在立了功開始學會咬人了,開始罵陸某狼子野心,嚴嵩是一個,你是一個,你們才是我大明朝的奸臣!」
「你、你!」
張經被懟的呼吸不暢,捂著心口悶哼一聲,隨即竟然是咳出了一口逆血出來。
衙堂外幾名張經的親兵見狀趕忙衝進來,可他們一動,更多的金吾衛也沖了進來,齊刷刷護在陸遠周圍嚴陣以待。
在南京城,誰敢動陸太傅。
「都出去!」
張經揮手,他的親兵便連忙退下,陸遠見狀也揮了揮手,帶來隨扈保衛的金吾衛亦是離開。
「陸閣老文官出身牙尖嘴利,善於顛倒黑白混淆視聽,這一點老夫不是對手。」
「張部堂這一番話就對了一個字,老,你就是老了,老糊塗了。」
既然張經都打算回到北京上疏彈劾自己陰謀不軌了,陸遠還憑什麼給張經留面子,哪能那麼賤啊。
最好給他氣死。
張經胸膛幾次起伏,壓住心火說道:「人在做天在看,皇上聖明灼照,能夠辨別忠奸。」
「忠奸?」陸遠呵呵低笑起來,隨後點頭:「對對對,皇上聖明一定能辨別忠奸,但是陸某奉勸張部堂,憑著這次剿滅汪逆的功勞,您老起碼能混一個世爵,非侯即伯,從朝堂歸隱頤養天年吧,別攪和了,攪到最後怕是忠名保不住,再給自己留一個奸名。」
「陸閣老真覺得能在我大明朝一手遮天了?」
「陸某沒這個本事也沒有這個心,陸某是皇上一手提拔上來的,報恩都來不及怎麼敢去做奸臣、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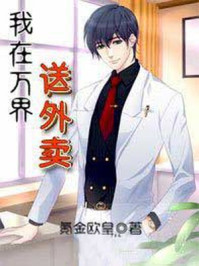 我在萬界送外賣 內容簡介:葉晨八歲那年,算命老道說:你十八歲那年將黃袍加身,天天山珍海味為伴!我信你個鬼你這糟老頭子!外賣員的黃顏色工作服也是黃袍加身?結果葉晨果真成了黃袍加身魚肉為伴的外賣員,不過……他的外
我在萬界送外賣 內容簡介:葉晨八歲那年,算命老道說:你十八歲那年將黃袍加身,天天山珍海味為伴!我信你個鬼你這糟老頭子!外賣員的黃顏色工作服也是黃袍加身?結果葉晨果真成了黃袍加身魚肉為伴的外賣員,不過……他的外 屍神鬼仙 開學軍訓,整齊的隊列方陣里總是多出來一個人。迎新典禮,赫然出現一個多年前的表演節目。集體上課,老教授為何一言不發。學生會換屆,為什麼沒有人去擔任宿管部長。宿舍查寢,看門的老大爺怎麼會是個道士。
屍神鬼仙 開學軍訓,整齊的隊列方陣里總是多出來一個人。迎新典禮,赫然出現一個多年前的表演節目。集體上課,老教授為何一言不發。學生會換屆,為什麼沒有人去擔任宿管部長。宿舍查寢,看門的老大爺怎麼會是個道士。 一擊魔法師 「世界上沒有什麼問題是一發火球術不能解決的。」
「如果有,那就兩發。」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世(dou)界(bi)級魔法師梅林凱恩·齊御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一擊魔法師 「世界上沒有什麼問題是一發火球術不能解決的。」
「如果有,那就兩發。」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世(dou)界(bi)級魔法師梅林凱恩·齊御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